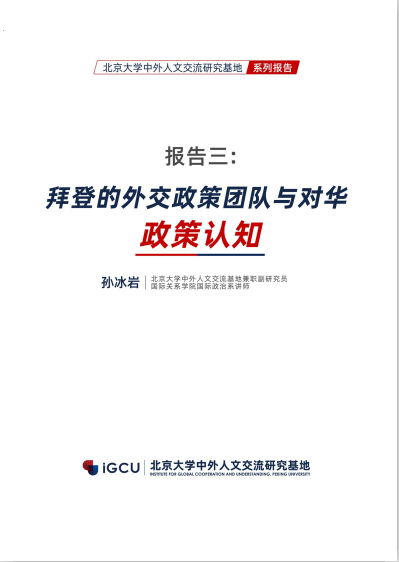
随着美国大选结束和拜登胜出成为当选总统(president-elect),下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已经显露出雏形。拜登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既对外交政策感兴趣又熟知外交知识的总统。拜登自1997年起就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期参与美国对外条约的缔结与外交官任命。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浸染21年后,因其丰富的外交知识和老成的外交经验,拜登在2008年被奥巴马挑选为副总统竞选搭档以弥补其在外交方面的短板。正是因为其将近30年参与外交事务的经历,拜登在美国外交政策界积累起广泛的人脉关系网,这使他在2020年大选中轻松组建起数量庞杂、组织有序、政策全面的外交政策团队。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拜登在竞选中组建的外交团队规模达到1000多人,拜登的竞选助手根据团队的不同专业领域将1000多人分为20个小组并在每组设立负责人,准备在拜登胜选后根据专业分组将组员们“填充”到合适的政府部门。在拜登已经胜选的情况下,通过梳理拜登外交团队中核心成员的政治派系,汇总拜登外交团队成员的主要政策观点,可以大概预判拜登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
一、拜登外交政策团队的组成与派系脉络
从团队成员在美国党派政治势力中的政治关系背景看,当前拜登外交政策团队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五个派系: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老臣”、拜登的嫡系“亲随”、民主党外交政策人才基干、反对特朗普的无党派职业外交家和共和党人、没有外交知识但会对拜登影响巨大的核心政治顾问。
首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外交“老臣”将构成拜登外交政策团队的主体,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拜登“内阁”级外交官员任命的主要群体。这些最核心的外交“老臣”包括苏珊·赖斯(Susan Rice)、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本·罗兹(Ben Rhodes)、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人。尽管都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且忠于民主党尤其是奥巴马的外交议程,这些“老臣”内部依然存在微妙的外交政策和派别分野。其中,苏珊·赖斯、鲍尔、罗兹最早加入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是奥巴马的政治亲信。三人是奥巴马坚定的追随者,是奥巴马在白宫期间最为信任的外交政策顾问,是奥巴马风格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也是最典型的“奥巴马主义者”(Obamians)。在对华政策方面,苏珊·赖斯、鲍尔和罗兹相对比较温和,他们在被媒体问到中美关系时始终强调中美依然存在合作点,但他们也主张美国应在人权、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升级制裁或施压。
与奥巴马主义者不同,沙利文、坎贝尔和弗卢努瓦无论在政治关系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都与希拉里更加亲近。年少有为的沙利文曾是希拉里最重要的外交顾问,在担任希拉里的幕僚长期间,国务院中曾流传着“如果事情重要,我们直接找杰克”( "If it's important, we just go to Jake.")的说法,足见希拉里对沙利文的信任与沙利文对希拉里的重要性。2013年希拉里为准备总统竞选而提前离开国务院后,沙利文并未跟随离开而是被托付给拜登,担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继续参与奥巴马政府重大外交政策的制定。2016年大选前,几乎所有媒体都预测沙利文将担任希拉里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国务卿。经历失望的2016大选后,沙利文回归民主党政策研究圈蛰伏,随后加入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为拜登的外交政策定调。拜登胜选后,沙利文再次被媒体认为是拜登侧近决策圈的核心人士。沙利文在对华政策方面温和与强硬共存,一方面认为中国不是苏联,中美关系不是冷战,美国可以与中国选择性的合作,另一方面主张美国应在技术创新、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加大与中国的竞争力度。
弗卢努瓦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甚至一度被奥巴马考虑提名国防部长。由于其对国防部专业精干的管理能力,以及国防部中少有的女性高官身份,弗卢努瓦在2016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国防部长的人。希拉里败选后,国防部长马蒂斯基于对弗卢努瓦业务能力的认可,曾向特朗普提出任命弗卢努瓦为副国防部长,但民主党党性强烈的弗卢努瓦婉拒了马蒂斯的邀请。离开国防部后,弗卢努瓦回到她参与建立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担任主席,招募那些被特朗普政府“放逐”的民主党专家官员。弗卢努瓦还利用自己与国防部的关系成立“政策顾问”公司,为美国企业和国防部的商业合同进行游说,为进入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提供风险咨询。加入拜登团队后,弗卢努瓦主要负责美国国防战略和政策方面的制定。拜登胜选后,弗卢努瓦再次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国防部长位置的最有力竞争者。由于主政美国国防战略的执行,弗卢努瓦在对华军事立场方面非常强硬,曾提出美国应大力发展军备以确保美军可以在72小时内击沉中国所有海军舰只的构想。
在国务院担任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在希拉里离开国务院后也很快离开,成为希拉里2016年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坎贝尔也曾被认为是希拉里政府国务卿的有力竞争者。希拉里败选后,坎贝尔转入民主党智库界,继续保持与民主党高层的联系。加入拜登团队后,坎贝尔和同样为拜登提供政策建议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成为团队内少数熟悉中国事务的核心顾问。在2016年希拉里被看好接替奥巴马的时候,坎贝尔出版专著《转向》以阐述民主党的重返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转向”(Pivot)实质上是对奥巴马亚太战略的延伸,坎贝尔在他的政策规划中甚至将中国作为可以美国继续对话与合作的一般性“伙伴”(partner)。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开始走低后,坎贝尔在2019年《外交》期刊上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承认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主张竞争性的政策应更多地被赋予到对华关系中。
其次,拜登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嫡系“亲随”可能成为影响拜登对外决策的关键力量,他们包括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埃弗尔·海因斯(Avril Haines)、科林·卡尔(Colin Kahl)、丹尼尔·贝奈姆(Daniel Benaim)、布莱恩·麦基恩(Brian McKeon)、杰弗里·普莱斯考特(Jeffrety Prescott)、卡林·蕾切尔(Carlyn Reichel)等。拜登最信任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布林肯、前中情局副局长海因斯从拜登在参议院时期就担任他的政策顾问。与奥巴马主义者相比,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方面立场相对强硬。今年9月在美国商会发表演讲时,布林肯称中美彻底脱钩是“不现实”和“彻底有害的”,但拜登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关税手段对华施压,中方应为当前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负责,美国领导人应更多地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接触以避免双方误判。海因斯当前被认为很有可能会领导中情局,其对中国的认知主要集中于网络安全和情报层面,认为中国近年来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对美国形成更大的国家安全挑战;蕾切尔从2015年起就开始为拜登撰写外交讲稿,并在2020年大选中负责核心竞选讲稿(如提名演讲)的撰写。蕾切尔有可能像奥巴马的撰稿人罗兹那样因为参与重要的外交稿件撰写而成为总统的核心决策成员;科林·卡尔和杰弗里·普莱斯考特担任过拜登的副总统外交顾问,随后又负责管理和招募拜登竞选外交团队,如宾大拜登中心;拉特纳在竞选期间参与拜登对华外交政策定调,也是拜登团队中针对中美关系发声最多的核心成员。在其发表在《外交》期刊的文章中,拉特纳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但认为中美不应脱钩而应“再调整”(recalibrate),美国的脱钩政策实际上是孤立自己,美国在经济上要防止军民两用技术流入中国军方手中,建议拜登政府对在美中概股动手,要求中概股企业如无法向美国证监会提交审计底稿就退市,美国应尽快设计在数字货币领域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计划;丹尼尔·贝奈姆和布莱恩·麦基隆在胜选后负责拜登过度政府外交成员的遴选。在以上这些拜登的政治“亲随”中,除年纪相对较大的布林肯(58岁)以外,其他成员整体上都属于比较年轻的70后,他们中的部分人并没有在奥巴马政府任职,或者只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过中层官员,因而在拜登政府中他们很可能会担任助理国务卿或重要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级别外交职务。从民主党对本党外交政策人才的提拔培养路径来看,这批属于拜登外交“亲随”的年轻外交专家极有可能在拜登离任后成为未来民主党政府外交议程的顶级决策者。
第三,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人才基干将成为填充拜登政府外交部门中层职位的主要群体,如助理国务卿及帮办、助理国防部长及帮办、国家安全委员会事务主任、总统特别助理、白宫顾问委员会成员等不属于最高层但提供最关键政策建议的职位。这批人曾在奥巴马或克林顿时期担任对外政策的研究和政策建议任务,他们从专业研究角度向民主党总统提供政策选项并制定议程计划,他们是确保民主党政府在外交领域“科学决策”的基干力量。特朗普执政后,在国务院、国防部、国安委、国土安全部、中情局甚至是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民主党外交基干很快被贴上“奥巴马党人”的标签,被特朗普赶出白宫。被特朗普“放逐”后,他们或者进入智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或者加入公司提供政策咨询。在拜登、布林肯和弗卢努瓦的努力下,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进步中心(CAP)、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宾大拜登中心招募网罗住大量奥巴马时期的民主党政策基干力量,从而为这批人在拜登参选后快速组建外交顾问团队打下组织基础。在这个被布林肯和弗卢努瓦网罗的群体中,有长期从事中东政策研究的著名专家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和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副国务卿的职业外交官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也有曾任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和曾任国安会亚洲主任、熟知朝鲜半岛问题的车维德(Victor Cha),有欧洲问题专家朱利安尼·史密斯(Julianne Smith),也有对华贸易政策专家伊丽莎白·罗森堡(Elizabeth Rosenberg)。对于信赖专业研究的拜登及其高层外交顾问来说,这批民主党外交政策基干将为拜登政府相对理性的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保障。
第四,反对特朗普的无党派职业外交家和共和党人也会成为拜登外交团队的一部分,典型的如自称无党派人士和职业外交人员的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和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二者在奥巴马时期分别担任副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如在今年大选期间以“十宗罪”联名谴责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共和党建制派专家;如曾在特朗普政府国防部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但与弗卢努瓦关系密切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这批人在外交政策立场上强烈谴责特朗普破坏美国联盟体系和退出国际组织的单边主义政策,批评特朗普将党派成见带入美国政府外事部门,认为特朗普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批评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没有“章法”和战略,造成美国商界的利益损失。基于此,他们从推翻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角度选择在2020年竞选中与民主党合作。对于拜登来说,职业外交官与共和党外交建制派的背书更能体现出他作为分歧弥合者的政治色彩。当然作为对共和党人公开背书的政治回报,拜登也会为这批反特朗普的共和党建制派安排外交职位,但他们对拜登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尚难判断。
第五,在本次竞选中帮助拜登拿下选举胜利的重要政治顾问很可能也会成为影响拜登外交政策的独特一派。在对外决策过程中,总统并非全部听从外交政策专家给出的建议,总统有时会听取最熟悉他心中所想的政治顾问们的建议,尽管他的政治顾问对外交事务所知不多。例如,奥巴马的白宫幕僚长并非外交政策专家,但他有时也能对奥巴马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特朗普刚刚入主白宫后,他原来在商界的老朋友反而对他的对华贸易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在竞选中出力最多的政治顾问很可能也会对拜登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如拜登的重要竞选顾问史蒂夫·雷切蒂(Steve Ricchetti)和安蒂娜·邓恩(Antina Dunn),如著名的竞选操盘手迈克尔·多尼隆(Mike Donilon,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兄弟)、拜登的前幕僚长罗恩·克莱因(Ron Klain)以及负责组建过渡团队的泰得·考夫曼(Ted Kaufman)。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可能不多,但他们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绝对不小。
二、拜登外交政策团队的对华政策共识
与特朗普封闭的决策圈与混乱的对外决策模式相比,拜登政府的对外决策很可能会回归正常状态,即在听取部门意见、比较不同观点、考虑多方诉求后做出最终决定。过多的政策顾问和决策选项可能会导致拜登在决策时面临选择犯难的烦恼,但基于民主党人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基本认可,拜登团队在诸多重要的外交议题如中美关系、美俄关系、联盟政策等方面的观点将会大同小异。尤其是在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政策主张方面,拜登团队内部存在诸多观点共识。
首先,拜登的外交团队成员更加积极地参与中美高层对话与中美人文交流,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顾问更加全面、多元和深入,这会直接影响到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在拜登团队中,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重要外交职务的多尼隆、苏珊·赖斯、沙利文、布林肯、罗兹、坎贝尔、拉塞尔都曾到访中国,他们或者直接与习近平主席有过会谈,或者与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领导人有过多次会面。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进行交流使他们可以理解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意图,不会在对华认知方面妖魔化中国或夸大中国威胁。在拜登团队中,很多职业外交官或外交专业人才都曾积极参与过中美学界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使他们对中国的外交观点与主张有着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如属于拜登侧近外交顾问的普莱斯考特早在2002年就在北京设立耶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分部办公室,他还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沙利文在希拉里败选后也曾短期来访中国,他在学术会议上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就中美关系进行过非常坦诚的交流。沙利文、坎贝尔、拉塞尔、拉特纳、科尔比等和中国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交流,也参加过由北京大学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科尔比甚至还与中国学者就中美战略关系合作撰写过学术论文。在学术交流过程中,这些学者一方面听取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阐释与解释,另一方面则向中国学者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很可能会促使即将进入拜登政府的美国外交决策基干更有可能从相对客观理性视角参与对华政策制定。
其次,拜登团队成员基本上都是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坚定信奉者,他们的对华政策会被置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视角下来考虑,具体到对华政策方面就是:对华政策是美国全球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框架的重要部分,即使中美已经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确保美国竞争优势的根本办法就是坚持美国领导全球多边机制和全球规则的构建。如果中国愿意服从遵守美国领导构建的全球制度规则,美国并不排斥中国加入。如果中国抵制美国领导的全球制度并试图“另起炉灶”构建新的规则与制度,美国将动用其当前在全球制度中的优势地位,联合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阻挠中国领导和制定全球制度与规则。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维,拜登团队主张在全球范围对中国的影响力进行抵制时,应注重联合美国的盟国、注重领导全球制度规则的改革、注重维持美国对规则的把控与领导能力,因为这才是美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并继续在全球维持霸权地位的根本原因。
第三,拜登的外交团队认为,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特朗普上台前的状态,由于中国实力的迅猛增长,中美两国已经进入全面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自尼克松政府开始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拜登政府需要在总的对华战略方面制定“新路径”(new approach)。根据沙利文和坎贝尔的观点,“新路径”的核心思路是“基于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的竞争与共存”(2019年二者发表在《外交》期刊上的文章)。根据拉特纳和罗森博格的观点,“新路径”的核心思路是更加积极地在贸易、全球制度、产业发展、人权与民主领域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但竞争必须是“良性竞争”(布林肯在今年接受采访时所用)。从拜登外交政策团队更多强调“竞争”的论述来看,拜登政府在诸多中美关系议题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很可能会比奥巴马时期要大。
第四,尽管都认为中美已经在全球范围开始大国竞争,但拜登团队成员认为赢得这场竞争的根本方式是解决美国国内问题、强大美国国内经济、增强美国国内创新力。因此,针对如何赢得未来与中国的竞争这个问题,拜登团队的核心成员如布林肯、沙利文、罗兹、拉特纳都从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个角度来提出对策,如解决国内种族问题、改革移民政策、吸引国际人才、加大产业技术(如人工智能、5G和区块链)研发领域的联邦政府投入、提升制造业工人工资、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联邦政府对本国制造业产品的采购力度等措施。拜登团队认为,美国发展模式的强大可以吸引其他国家自愿加入美国的发展模式阵营,这比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全球范围奔走劝说其他国家不要选择中国发展模式和项目(如一带一路)要更加有效,虽然拜登政府也不会放弃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中国发展项目的努力。
第五,拜登团队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认知可以被总结为两个“错误”和两个“但是”,即:(1)以冷战模式对待中美关系是错误的,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但是美国需要从维持其全球霸权的角度削弱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尤其是科技进步速度,防止中国在科技、经济和军事领域超过美国。因此,拉特纳等人认为,美国必须继续对中国在技术领域进行封锁限制,具体包括继续要求商务部制定更加严格的限制对华出口技术清单和产品门类,防止中国在核心产业技术(尤其是芯片制造)方面实现产业自主,联合美国的盟国共同限制对华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以限制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联合美国的盟国共同研发5G技术与其他新兴产业技术;(2)彻底的中美经济脱钩是错误的,彻底脱钩对美国经济也不利,但是拜登政府应以国家安全视角重新审视其是否在经贸领域对中国存在依赖,尤其是在关键性的产业供应链方面是否对中国存在依赖,重新审视美国与中国的技术贸易是否会影响美国的产业优势。拜登政府应增强美国在重要产业供应链方面的自主性,如关系到尖端武器制造的稀土产业与关系到美国生物安全和健康的卫生防疫产业。同时,美国应加强对未来中美企业并购和技术交易的审查力度,严防先进技术落入中国企业手中。
第六,在对中国进行定位时,拜登团队已经不再像奥巴马政府那样将中国定位为一般性伙伴(partner),但拜登团队也认为中国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敌人”(adversary)。因此,拜登团队一方面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公开把颠覆中国国内政治制度作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则会强调中美同样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强调中美可以进行选择性合作,尤其是强调中美应避免恶性竞争所导致的军事冲突。正如苏珊·赖斯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在当前,我不确信我能否还能使用‘信任’这个词来定义对华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共同合作。”基于此,拜登政府会在加大对华军事、技术和全球影响力打压力度的同时,也可能会在某些议题领域选择性地与中国进行合作,如气候变化、疫情防控、伊核协议、朝核问题等议题。在避免中美因恶性竞争而产生军事冲突方面,拜登团队认为中美必须加强对话,通过面对面交流不断地澄清两军在某些敏感热点地区的底线和意图。正如多尼隆所说,中美构建“健康、稳定和可靠的中美两军关系”非常必要。
第七,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拜登外交政策团队的涉华观点固然值得关注,但从拜登外交政策团队尤其是核心成员已经表达出的外交观点来看,在他们对美国外交议程优先性的排名中似乎并未将对华政策作为拜登政府的最优先议题。在拜登团队看来,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对华政策并非最紧急和最需要拜登政府做出改变的议题。如果从拜登团队在胜选前所发表的政策观点来看,对特朗普时期糟糕混乱的外交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将是拜登政府最先执行的外交行动,这些可能被拜登政府最先“拨乱反正”的议题包括:撤销特朗普对美国盟国(主要是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税、恢复美国与北约和日本的关系、重新加入特朗普已经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和其他国际组织、重新评估特朗普时期的中东政策(巴以问题、与沙特的关系)、考虑重建伊核协议的可能性等,其中,对特朗普时期恶化的中美关系进行明显的“拨乱反正”似乎没有出现在拜登团队的政策优先议程中,改善中美贸易关系尤其是撤销对华关税(哪怕是部分)并没有出现在拜登团队竞选期间的言论中,这也说明中美关系很可能不会是拜登上台后优先作出改变的政策议题,拜登团队也有可能愿意继续维持特朗普时期遗留的对华贸易施压措施,争取在未来的中美谈判中保留足够的谈判筹码。如此看来,拜登政府初期的中美关系有可能会出现相互观望和试探的状态,尤其是拜登政府可能不会急于快速撤回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而是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对中国是否愿意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作出实质性让步(产业补贴、汇率政策、开放投资市场)进行耐心的观望。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如何在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和中美关系前途未卜的背景下主动“破局”将成为考验中美关系的关键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