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和可能的“是”——海德格尔思想重探》这部著作,不是对已有海德格尔研究成果的一般性总结和梳理,而是从他的“是论”出发,对其思想加以重构的尝试。当然,有了确定的视角,在能够清晰展示出海德格尔思想中某些侧面的同时,必定也会隐去另外一些也许同样重要的侧面,但这是理论工作本身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认为“是”的具体性、可变性与可能性是海德格尔“是论”的核心,而他呼唤的“另一个开端”,就意味着从这一立场出发,重新把握人与物及历史、当下与未来,以创造一种全新的思想。由此反观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就可以看出后者的根本特点则是试图从普遍性、不变性和确定性的角度对人与物的本质加以认识和规定。从这个视角出发,海德格尔思想中很多原本让人感到晦涩难解甚至矛盾扞格之处都可以得到合理克服,虚无主义的问题自然也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当然,如此理解的海德格尔思想,还体现出与中国传统哲学显而易见的遥相呼应,中西两大思想传统未来可能的交汇与激荡已呼之欲出。
本书除“前言”和“余论”之外共八章。“前言”从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出发,勾画了海德格尔思想得以展开的历史背景,揭示了那个时代给思想提出的根本任务,并初步提示了“是”问题的含义。另外,“前言”也对本书解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语言的方式进行了简要说明,强调本书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倾听”与“因应”,是用海德格尔自己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阐明的一种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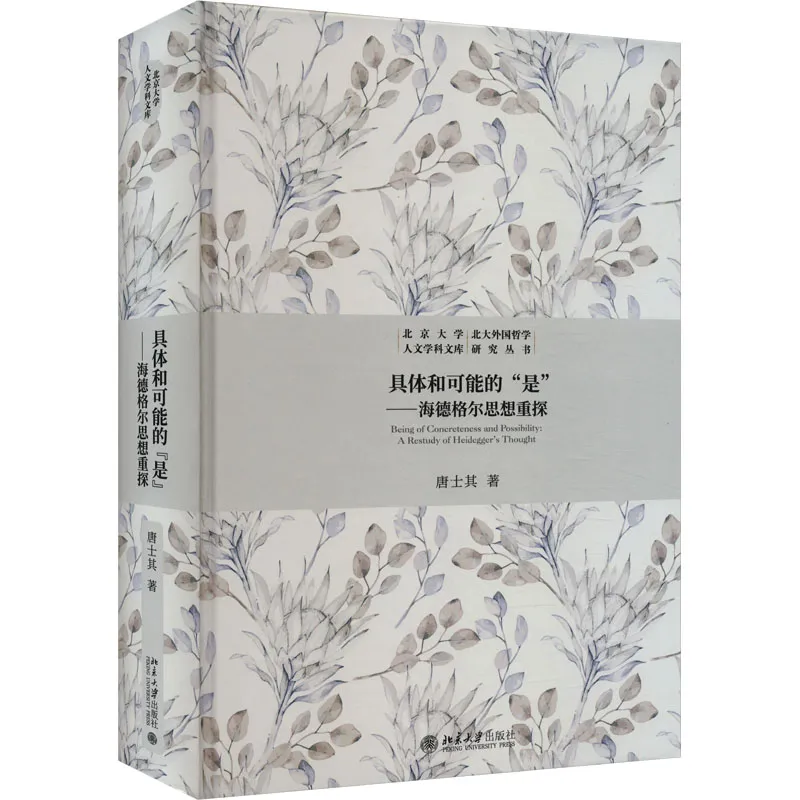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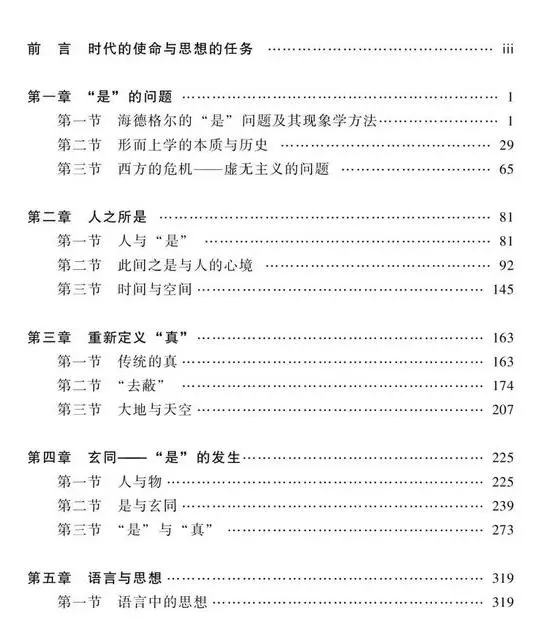
第一章“‘是’的问题”是对海德格尔“是论”的初步阐发,通过展开“是者之所是”与“是”本身之间的“是论差异”呈现了“是”的独特性,并且讨论了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对西方思想和精神危机之根源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形而上学追求的基本目标即物之本质就是“是者之所是”,比如柏拉图的“型相”、黑格尔的“理念”,以及尼采的“力量意志”等。这个“所是”实际上也是一种“是者”,它对“是”本身的替代最终导致了人对“是”的遗忘与“是”对“是者”的离弃。从终极意义上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的是万事万物之后某种作为其“是”之根据的至高至上的“是者”,但思想的展开却不断证明这一具有最高确定性的“是者”并不存在,这个发现最终导致了体现为虚无主义的西方思想的危机。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否定物具有任何确定的根据。它的出现,毫无疑问意味着形而上学即西方传统思想的终结。这不仅是西方思想的危机,而且也意味着西方人的精神和伦理危机。要摆脱这种危机,出路显然不在于再一次去寻找什么不同的方法以确认那个最高的“是者”,而是从根本上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因此呼唤“另一个开端”。这一章还介绍了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传统中两个核心概念即理性和逻各斯含义流变的考证和梳理,即前者从“直觉”转变为“算计”,后者从“采集”转变为语言性陈述及其规则。这两个转变都是西方思想演化过程中的标志性环节,其结果则是古希腊思想原本包含的创造性可能丧失殆尽。
第二章“人之所是”通过介绍海德格尔对人之“是”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其“是论”的基本内容。海德格尔从一种特殊的、能够对“是”进行提问并加以体验的“是者”即人出发,原本希望通过对人之“是”以及如何“是”的考察,为对“是”之一般的研究奠定基础。因此,他对人之所“是”的基本特征即所谓的“生存表达”,比如牵挂、惶恐、罪欠等,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而这些所谓的“生存论分析”全部指向人之“是”的条件性、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这样,“人是什么”这一抽象问题实际上就转变为“人是谁”这一具体问题。至于造成这种条件性、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的根源,则是人之“是”所具有的时间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性就是“是”的可变性,因此时间并非如牛顿所理解的那种类似空间的、事物变化得以在其中展开的均质的维度。对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来说, “生存表达”研究的意义在于使他明确了“是”之一般的基本特性。
第三章“重新定义‘真’”阐发了海德格尔关于“所是”之“是”和“是”之“所是”的思想。传统上,这一章的内容可以被归结为“真理的本质”。本书之所以放弃了“真理”这样的表述,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真”是物的一种状态,而并非两物彼此相符的关系(传统上对“真”的理解);另外,“真”作为遮蔽的去除即“去蔽”,显然与“理”即物之逻各斯拉开了距离。“真”意味着物以其自身面目示人。但是,要让物以自身面目示人,就需要某个开放的领域让光通过,这就是所谓的“通透”。当人获得这种“通透”,当物在“通透”中以自身面目示人,人就得到物之“真”。在海德格尔看来,物之“真”的呈现也就是物之“是”的发生。“是”在通透中发生,因此,“真”就是“是”之通透的发生。海德格尔在此还阐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真”也就是“是”之通透永远不可能以完全、纯粹、一劳永逸的方式发生,因为通透与遮蔽相生相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海德格尔称之为“天空”与“大地”,它们分别代表了遮蔽与通透、收纳与拓展的力量。因此,“去蔽”就成为一场斗争,意味着把物从遮蔽中争取出来。这也意味着物永远不会以其全貌示人,人对物的了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不完整性。
第四章“玄同——‘是’的发生”是全书的核心,也是对海德格尔“是论”的全面阐释。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是一种发生,是天地神人“四象”,即通透与遮蔽、人与人之可能性某种特定组合的结果。它们聚于某一物,比如装葡萄酒的壶。因此,“是”的发生一定是物性的某种自然“涌出” (即古希腊语中“自然”一词的本义),从而具有具体性、可变性,并且充满了可能性。这一发生就是“玄同”。“玄同”这一译名取自《老子》,意为人与物完全的合二为一。玄同的发生如同一道掠过黑暗的电光,使世界以某种特定的面貌显现在人的眼前。具体说,玄同又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是”的整体性发生,意味着玄同为某个时代、某种特定条件下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提供基础,这种意义上的玄同类似于库恩的“范式”或者尼采的“视域”;另一方面则是某一具体物之“是”的发生,在此意义上的玄同即人的思想与某物之“是”的共振,所以海德格尔强调是与思想的同一性。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关于玄同的思想已经强烈地暗示,玄同本身并没有任何先定的基础,因此从玄同的角度理解的“是”,就是没有先定基础的“是”。
第五章“语言与思想”阐释和梳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考。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讨论在其晚年的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促成了这些学科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海德格尔之所以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不仅因为西方传统上把人视为“会说话的动物”,更因为在他看来,“是”或者“玄同”只能在语言中发生,所以“语言乃‘是’之家”。当然,这里的语言不仅指通常意义上书写或者语音表达的语言,更指人的表达本身,所以是“广义”的语言。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想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他认为语言固然是思想的表达手段,但要真正懂得语言的表达,还需要理解语言性表达所没有、所不能传达的意蕴,这就是所谓的“示喻”。从某种意义上说,“示喻”比声音和形象的表达更具根本性,因而是本源意义上的语言。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强调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即“示喻”并非对已经存在的思想的事后表达,相反,思想是对示喻的因应,而本源性的语言就是“是”的发生,因为奠基性的语言,比如诗人的语言,就是玄同本身。思想本质上是对语言的倾听,真正的思想是静默中的思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第六章“民族、历史、国家与政治”集中分析海德格尔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作为海德格尔“是论”的体现,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自然强调民族、历史和国家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强调政治在一个民族独有的历史中对其命运的把控与创造。作为一切创造性中最具创造性的行动,特别是建国和奠基,政治具有开创或者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可能。因为“是”是一种玄同,而玄同并没有特别的基础,所以海德格尔强调政治中的决断。在他看来,真正的决断,恰恰是对决断的理由本身的决断。这种决断体现在他本人身上,就是对纳粹主义运动的断然参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是他的思想中最晦暗和最浅薄的部分。这并非因为他对纳粹主义运动参与的失败,而是因为他的政治思想从整体上看恰恰背离了他的哲学中那些最令人着迷的内容,即对“是”的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的关切。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海德格尔政治上和政治思想上的失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证明了他的哲学思想的价值。
第七章“对技术时代的批判”总结和分析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固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去蔽即对物之“真”的揭示,但并非物自身的呈现,而是根据人对物的某种先定的理解即所谓的“数学性知识”对物的对象化和操纵。技术对物的摆置(可以简单理解为出于某种目的对物的刻意摆放和安置)恰恰表明了现代科学的本质。技术带来了物质财富的丰裕与人类生活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破坏,以及技术社会对人本身的全面奴役。在技术的发展中,人失去了自身的根本,即与自然、与大地的血肉联系。当然,这种技术观包含了海德格尔自身的偏见,即他对乡土、对大地的执念和对工业社会的陌异,但也体现出他对世人的警醒。它让人反思人之为人的根本以及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关系。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位反智主义者,他也清楚无法单纯地阻止科学技术的进步,但他呼吁人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保持对技术的独立性,即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同时,海德格尔依据遮蔽与去蔽、天空与大地相伴相依的关系也认为,或许技术发展的极致,可以为人们带来一次新的玄同。
第八章“未来的思想”是对全书内容的收束,也是对海德格尔一些隐而未发的思想的引申。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已经终结于尼采的虚无主义,所以他致力于探索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思想即“另一个开端”的可能。这种思想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首先,它超越了简单的形式逻辑即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因而是一种体现“有无相生”的基本原则的思想。它主张“有”的根据就是“无”,是“无极之基”。其次,它的具体进程体现为“同一性的反复”,因而是一种可以摆脱传统思想的轨道,不再需要通过本质概念对物加以规定,并且通过反复归因,最后终结于某个神秘的“第一因”的思想。总体而言,这种新思想全面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并且终于在西方思想的延长线上承认并接纳了自其开端处就避犹不及的“无”。海德格尔对“无极之基”的反复阐释表明,这是非基础的基础、无根据的根据,是动态的、有条件的、天地神人“四象”相互依赖的基础和根据,是玄同。在此,海德格尔走向了他在早年就一直期盼的与东方思想的交融。
“余论”探讨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三个具体问题。首先是世界的真实性。海德格尔实际上取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离开人追问世界的真实性毫无意义。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态度归结为唯心主义,因为这是海德格尔“是论”的体现。其次是东西方的对话。海德格尔一方面认为只有东西方思想的对话才能提供一条解决西方思想危机的出路,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此之前,西方首先必须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东方也需要摆脱业已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并回归自身的本源。最后是关于神的问题。虽然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神”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但实际上他基本没有在传统宗教的意义上理解他所说的“神”。对海德格尔来说,“神”意味着人未知的可能。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在时代困境下“玄同”如何发生,新的思想如何创造,关于这些问题虽然人们很可能非常迫切地希望获得某种答案,或者哪怕是些许暗示,但我们也只能保持谨慎的沉默。如果说海德格尔提供了某种指引,那也只能是“因应”:因应时代,因应大众,因应思想本身。
(本文摘自唐士其所著的《具体和可能的“是”——海德格尔思想重探》(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后记》)